本文目录一览:
詹姆斯·乔伊斯的生平
詹姆斯·乔伊斯
爱尔兰作家 ,诗人 。1882 年2月2日生于都伯林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941 年1月13日卒于瑞士苏黎世 。先后就读于都柏林大学克朗格斯伍德学院、贝尔沃迪尔学院和大学学院,很早就显露出音乐、宗教哲学及语言文学方面的才能,并开始诗歌、散文习作。他谙熟欧洲大陆作家作品,受易卜生影响尤深,并渐渐表现出对人类精神世界特殊的感悟及对家庭笃信的宗教和自己生活环境中的习俗、传统的叛逆。1902年大学毕业后,曾与当时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有所接触,不久即成为其对立面。同年,迫于经济压力及为摆脱家庭宗教和自身狭隘环境的束缚,自行流亡到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过着流离的生活,广泛地吸取欧洲大陆和世界文化的精华。前档胡1905年以后,携妻子儿女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定居,带病坚持文学创作詹姆斯•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生平与作品
1882年2月2日,乔伊斯(James Joyce)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父亲对民族主义有坚定的信念,母亲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乔伊斯出生的时候,爱尔兰这个风光绮丽的岛国是英国的殖民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有一大群弟弟妹妹,但他父亲偏爱这个才华横溢的长子,“不论这一家人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也给他钱去买外国书籍。”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天主教教育,学习成绩出众,并初步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1898年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和语言,1902年6月,乔伊斯毕业于都柏林大学学院,获得了现代语学士学位。10月2日,他登蠢余记到圣西希莉亚医学院修课。可是,在这里只念到11月初就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了学业。1904年,他偕女友诺拉私奔欧洲大陆,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长及一生的流亡生涯,中间仅仅点缀着短期的回乡探亲,1911年后便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他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的里雅斯特、罗马、巴黎等地,多以教授英语和为报刊撰稿糊口,又饱受眼疾折磨,到晚年几乎完全失明;但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勤奋写作,终成一代巨匠。1939年巴黎沦陷,12月他带着家眷疏散到法国南部。1940年12月17日,乔伊斯夫妇把患精神分裂病的女儿露西亚留在法国的一家医院,狼狈不堪地逃到瑞士的苏黎世。第二年的1月10日,乔伊斯因腹部痉挛住院,查明是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在13日凌晨去世,终年59岁。
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他1904年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这本书的创作原则:“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这实际上也成了他一生文学追求的目标。在乔伊斯眼中,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和钳制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而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每时每地都上演着麻木、苦闷、沦落的一幕幕活剧。
詹姆斯•乔依斯于1904年1月7日,在他母亲逝世之后4个月起在都柏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1914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历时10年。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主要描写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如何试图摆脱妨碍他的发展的各种影响——家庭束缚、宗教传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去追求艺术与美的真谛。乔伊斯通过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故事,实际上提出了艺术家与社会、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并且饶有趣味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斯蒂芬•迪达勒斯本人恰恰就是他力图逃避的都柏林世界所造就的,都柏林无形中报复了反叛的青年艺术家。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一生中平凡一天的记录,即主人公广告经纪人利奥波德•慧拦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一天的活动。乔伊斯在本书中将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铸于一炉,借用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的框架,把布卢姆一天18小时在都柏林的游荡比作希腊史诗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使《尤利西斯》具有了现代史诗的概括性。《尤利西斯》以三个人物为主,除代表庸人主义的布卢姆外,还有他的妻子、代表肉欲主义的莫莉以及代表虚无主义的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小说通过这三个人一天的生活,把他们的全部历史、全部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长篇小说《芬尼根守夜人》以都柏林近郊一家酒店老板的潜意识和梦幻为线索,是一部用梦幻的语言写成的梦幻的作品。乔伊斯借用意大利18世纪思想家维柯关于世界在四种不同社会形态中循环的观点,在此框架中展开庞杂的内容。书中暗喻《圣经》、莎士比亚、古代宗教、近代历史、都柏林地方志等,大量借用外国词语甚至自造词汇,通过夸张的联想,喻示爱尔兰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全宇宙的运动。�
除上述三部作品,乔伊斯还著有诗集《室内乐集》和剧本《流亡者》。�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思想是贯彻始终的。早在1912年8月22日,刚届而立之年的乔伊斯就在致妻子诺拉的信中写道:“我是也许终于在这个不幸的民族的灵魂中铸造了一颗良心的这一代作家之一。”1936年,乔伊斯边读着英国版《尤利西斯》的校样边对弗里斯•莫勒说:他为了这一天,“已斗了二十年”。 乔伊斯从1914年着手写《尤利西斯》,但直到1918年美国的《小评论》才开始连载。最早的单行本是1922年在法国由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德(1927)、法(1929)、日(1932年出四分册,1935年出第五分册)译本相继问世后,美国版(兰登书屋,1934)也出版。然而对乔伊斯来说,最重要的是《尤利西斯》在英国本土的出版。也难怪他对丹麦诗人、小说家汤姆•克里斯滕森说:“现在,英国和我之间展开的战争结束了,而我是胜利者。”他指的是,尽管《尤利西斯》里对1901年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及太子(当时〔1904〕在位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均有不少贬词,英国最终不得不承认这本书,让它一字不删地出版。
乔伊斯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深深感动着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人是这么崇拜乔伊斯的,甚至把《尤利西斯》中描写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一天全部活动的六月十六日定为“布卢姆日”,该节日后来成为了仅次于国庆日(三月十七日圣巴特里克节)的大节日。
乔伊斯进入中国文学界的视野
“意识流”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随后便被借用到了文学领域。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就是意识流作品的代表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20世纪中国文学曾受到西方意识流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意识流文学。“意识流”这一概念进入中国语境经由两条路线:一条由西方先“流”到日本,再由日本“流”到中国;另一条则由西方直接“流”到中国。在时间上,前者稍早于后者。因此,我们在考察意识流进入中国之前,首先应当检查意识流是如何进入日本文化语境的。最早把乔伊斯介绍到日本的是当时活跃在日本和欧美的著名诗人野口米次郎(1875-1947)。他于1918年3月,在著名杂志《学灯》发表了介绍乔伊斯《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的文章《一个画家的肖像》。他称赞“这部小说是用英语写成的近代名作”。 另外,较早留下了关于乔伊斯记载的是芥川龙之介。他刊登在《三S》(《サンエス》1920年3月号)杂志上的文章《〈我鬼窟日录〉摘抄》谈到他曾购买丸善书店发行的《年轻艺术家的肖像》。并在1920年9月发表于《人间》杂志的《〈杂笔〉中的“孩子”》中这样谈到乔伊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无论如何看都是对儿童感受的直接述写。或者也许可以说是具有那种只要有一点感受就写下来的心情吧。但是无论怎样珍品就是珍品,像他这样写文章的找不到第二个。我想,读一读是有好处的。(8月20日)”
正因为如此,他后来还亲自翻译了《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的一部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密切,日本文坛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关注和译介很快就被中国知识界注意到了。不过,日本人最初对意识流的介绍和把握并不准确。1933年由高明翻译的早稻田教授吉江乔松撰写的《西洋文学概论》便将普鲁斯特与乔伊斯归为超现实主义流派。朱云影在《现代》(第3卷第1期)上写了一则《日本通信》:“‘新心理派’以伊藤整等为代表,虽然出了几种同人杂志,理论宣传得颇热闹,但是作品简直没有,倒是翻译的朱易士(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非常畅销,正宗白鸟曾推森欧外翻译的《即兴诗人》为明治时代的最大杰作,那么这里也不妨认为《尤利西斯》为新心理派的杰作了。 ”
乔伊斯及其《尤利西斯》就这样经由日本来到了中国。
高明撰写的《一九三三年的欧美文坛》中有这样一段:“朱伊士在‘Transition’杂志上连载了‘Work in Progress’。在尝试着英语革命的点上,被人注目着。有时候把字连在一起,有时候利用句子所有的联想:看他的意思像是在表现上开一新境地。他也许是说,‘新的感觉需要新的字眼’吧?在那里同时附着新字辞解;因为在那文章里,不加解释,是没有理解的可能的。”文中“Work in Progress”指的是乔伊斯的最后一部小说《为芬尼根守灵》,该书1927年起在杂志上连载,1939年出版。在文章末尾作者注明道,本文“系根据1934年日本中央公论年报写成”。这又一次证明乔伊斯是辗转日本来到中国的。
中国文学界与乔伊斯作品
在《尤利西斯》出版的当年,在剑桥留学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就读到了这部作品,并在他的《康桥西野暮色》前言中称赞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他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奔放的语言歌颂该书最后没有标点的一章:"那真是纯粹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傲面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泄,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
1922 年,茅盾先生在《小说月报》第13 卷11 号上撰短文介绍詹姆斯•乔伊斯的新作《尤利西斯》:新近乔安司(James Joyce) 的“Ulysses”单行本问世,又显示了两方面的不一致。乔安司是一个准“大主义”的美国新作家。“Ulysses”先在《小评论》上分期登过: 那时就有些“流俗的”读者写信到这自号“不求同于流俗之嗜好”的《小评论》编辑部责问,并且也有谩骂的话。然而同时有一部分的青年却热心地赞美这书。英国的青年对于乔安司亦有好感: 这大概是威尔士赞“A Portraitof the Artist as a YoungMan”(亦乔氏著作,略早于Ulysses)的结果。可是大批评家培那(Arnold Bennett) 新近做了一篇论文, 对于Ulysses 很不满意了。他请出传统的“小说规律”来,指责Ulysses 里面的散漫的断句的写法为不合体裁了。虽然他也说:“此书最好的几节文字是不朽,”但贬多于褒,终不能说他是赞许这部”。
30年代现代主义在中国掀起第二次高潮,大背景下零散的乔伊斯介绍文字略见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两篇不长的专论,乔氏的短篇“Counterpart”也首次完整地翻译过来。两篇专论立足点全然不同,因此所描述的乔氏亦判然有别。第一篇评述是费鉴照撰写的《爱尔兰作家乔欧斯》。⑧此文不曾预设乔是进步的或者颓废的,持论比较客观。费文介绍了《杜白林人》和《画像》,重点放在《游离散思》(即Ulysses) 上。费文尝试解读乔,少数地方略见切入,但总体不成功(篇幅短是一个原因) ,围着乔伊斯转一圈而已。此文认为《尤》“是一部包罗近代世界的一切———政治,宗教,实际,人道主义等等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但认为不能说该书是一种“新的”,而且有明显的缺点: 一是“重局部而忽略整个的谐和”,二是“注重人的肉体方面,而忽略精神方面”。虽然以今天的角度看,费所说的缺点属于误读,但费是读过原著来尝试批评的。费文的缺点是下功夫不够,将乔当作一般作家来阅读,说到底是缺乏真正的兴趣。
另一篇专论是周立波1935 年5 月6 日在《申报•自由谈》上揭载的《詹姆斯乔易斯》。文章前半部分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乔氏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乔的生活道路,其创作的流变与发展;主要的评述基本符合事实,但认为《画像》“没有独创的地方”。文章的后半部分问题却很大。周看乔伊斯的出发点,与苏联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里的观点完全一致,连所用的基本贬词(如“颓废”) 也完全相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受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苏联在1935年首译《尤》,只选译第一至第十节,刊苏联《世界文学》杂志,因此可以认为,立波写此文跟苏联选译《尤》有关,其资料来源来自苏联,并没有立波自己的意见,立波本人也未读过原著,lv 因此连误读亦无从说起,误读的源头在苏联。周立波与早期茅盾、徐志摩、费鉴照、赵景深、赵家璧、杨昌溪等人的评述或译述有很大不同,从影响源方面看,后者的基本观点是西方的,前者则是苏联的,前者武断主观,后者的批评充满迟疑和困惑,批评对象把握不住,语焉不详之处甚多;前者则是清楚明白的持否定态度。周立波此文的观点在40 年代后半、以及50 —60 年代逐步演成压倒一切的主调。
傅东华译的《复本》(即Counterpart) 当为乔氏小说的首次汉译。译文前有译者以否定的笔调写的约四五百言的简介,译文本身有傅一贯的流畅,内容大致查看下来亦无甚大不妥。在那一期的《文学》(2 卷3 期) 上还刊出中年乔伊斯的相片一帧和漫画一幅。
中国另一次对乔氏作品的翻译,是一份影响似乎不太大、只出了10 期的文学刊物《西洋文学》。这份创刊于1940 年的刊物为乔伊斯作品在中国再次试探性登陆做出过重要贡献。该刊在1941年推出“乔易斯特辑”,内有乔易斯像、乔的诗选、短篇《一件惨事》和《友律色斯》(Ulysses) 插话三节,还有翻译的爱德蒙•威尔逊( Ed2mund Wilson) 的《乔易斯论》。该刊还在“书评栏”里发了署名兴华的书论,介绍1939 年才问世的《斐尼根的醒来》。据该刊主要编辑之一张芝联介绍,该杂志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译文”,从它推出的托尔斯泰特辑、叶芝特辑和乔伊斯特辑来看,从它发表译作的译者队伍来看,这个短命的杂志其实在当时算得上一份高品位译文杂志,它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徐志摩等主编的《新月》一样,同具一份学人的高雅格调,惜乎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在翻译文学史上以及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1949 年后至1978 年30 年间,连上面这种“杂碎”似的介绍几乎都见不到了,即便是偶尔提到,乔伊斯也像是一具散发着恶臭的腐尸。
1950年11月,朱光潜先生在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起源》译后补记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朱先生虽没有直接评论本书,但否定了哈拉普视《尤利西斯》是运用传统的一个最好说明,而且是几个世纪文学发展最高峰的观点。1964年袁可嘉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上发表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对《尤利西斯》也持批判态度。
1978 年创刊的《外国文艺》享有一份光荣,即该刊在1980 年第4 期上发了3 篇乔伊斯短篇小说,即《死者》(王智量[ 智量]译) 、《阿拉比》和《小人物》(宗白译) 。3 个短篇选目出手不凡,其中前2篇是世界文学的短篇精品。这大概是新时期发表的对乔氏作品最早的译介。
该书初版半个世纪之后的1979年,钱钟书先生在所著的《管锥编》(第一册的394页)中用《尤利西斯》第十五章的词句(乔伊斯将yes和no 改造为nes,yo)解释了《史记》中的话。1981年,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作品选》第二册关于意识流的部分收入了《尤利西斯》第二章的中译,并附有袁本人的短评,对于该书的文学价值和地位重新给予了肯定。
资深翻译家黄雨石先生默默工作,他译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已由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年出版。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乔氏作品单行本,亦是大陆译介乔伊斯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1984 年10 月,孙梁译的《都柏林人》7 个短篇加上宗白等人人的其他8篇译作,,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都柏林人》之名出版。
80 年代最早的《尤》选译,是金 译的第二章,收入袁可嘉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 ;5 年后《世界文学》揭载金译《尤》的第二、六、十章和第十八章片断; 越年,百花出版社推出《尤》的选译本,并且增加了第十五章的片断译文。这些是中国第二次《尤》的选译,是在研读的基础上选译的,量与质均较高。
九十年代中叶,意识流开山之作、长篇巨著《尤利西斯》有了两部全译本:萧乾、文洁若合译的由南京译林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金盽所译的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至1996年)。
图书网:
151、朗读者-痛
痛苦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语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羡瞎,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中国古代文人,有多少沉郁顿挫的痛,就有多少达观不屈的逆境重生。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也是在其后的逆境中被推上了写作的巅峰: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即便我们在最恶劣的境遇,我们仍然有着不可被剥夺的精神的自由,可以选择以尊严的方式面对痛苦,而这种选择本身就彰显着人性的高贵。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和智慧,只有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由痛苦转换而成的财富。
导演宁浩,在疯狂的石头成名之前,也有过很多痛苦的经历,不一定都是失败,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商业成功而已。自信,都是从摔倒了再爬起来的过程中建立的。
女童保护组织孙雪梅,曾经是记者,公益组织,童年阴影,不敢身后有人的心底畏惧。猥亵案,在全国此起彼伏,只是法院公布的就有每天七起,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中百分之十是男童。
新东方俞敏洪,尽力而为是面对痛苦的一种态度。第三年复读,极度的拼命,目标是地区师范学院,结果考上了北京大学。一个人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变,完全变了一个人。
芭蕾舞谭元元,个人职业成就几近巅峰。人,不管走多远,回首总是身边的那些身影羁绊守护着我们。那山,那水,那人,都是基于回忆的故土吧!根在未亡人,或者已故的那些我们不敢忘记的亲人。
翻译家王智量,你想要获得幸福吗,那你得先饱尝痛苦。北大毕业,坚持翻译。回忆母亲的时候,饱含泪水和感情。母亲的恩情,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如果对母亲不好,就不配做人。人历袜懂忏悔,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能不被社会玷污。90岁老人的伟大母亲。非常懂得感恩。圣人!
穿越痛苦的办法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理解它到底兄烂空意味着什么。倒也不必始终将痛拒之门外,唯一要做的是不要忘记给自己点燃一盏叫希望的灯火。灾难的姐妹,希望永远会唤醒勇气和欢乐。
王智量的老伴是谁
吴妹娟。
1958年,王智量因“白专道路”被补划"右派",与妻子吴妹娟放河北山区改造,继发配至甘肃农村。
王智量1928年出生于陕西汉中,是我国著缓粗名的外文专陵袜家、尺哪激翻译家、小说家。
有一位母亲穿着破烂的衣服′去看儿子是什么节目
母亲走了七十里路去看他,他却嫌母亲穿得破旧怕同学看见……
极目新闻
极目新闻
4年前 · 楚天都市报官方账号
文章图片1
最新一期的《朗读者》的主题词是“痛”,节目请来了知名翻译家——王智量先生。他老人家已经九十高龄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他翻译的,至今还在出版。
文章图片2
王智量在访谈中讲到了自己的成长的故事,比如,没有吃的时候,常常是母亲不吃饭,才养大了孩子们。
董卿问王老,
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情?
王智量回忆,他还是个孩童在家乡上学时,有一次下课间坐在教室门口,远远看见一个老太太走过来,好像就是母亲。因为母亲穿得比较破烂,他怕同学看见笑话他,立马用身体遮挡住同学的视线,不让母亲和同学见面。
到了年末,过农历年春节的时候基仔,枯锋肢母亲问他,这一年有没有做过什么错事?
王智量还茫然不知,以为母亲没有洞悉那件事。
谁料母亲将这件事点破,并告诉他,当时是听说他在学校病了,便走了七十里路到学校去看他,而他却嫌弃母亲穿得破旧让母亲回去,第二天母亲又走了七十里路回家。
“幸亏有母亲教育了我,我才没有成为那种没有良心的人,没有成为一个坏人。”王老说,他后来就跪在祖宗牌位前忏悔,并一生引以为戒。
文章图片3
“如果有人不爱自己的母亲,那他就不配做人!”王智量在节目中大声说。
最近,湖北诗人余秀华出版了自己的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对母亲,她也有太多的话想说。
文章图片4
余秀华,1976年生于湖北荆门横店村。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那一年,因为母亲难产,余秀华从生下来就罹患脑瘫。
别人家的小孩都是跑跑跳跳地去上学,余秀华上小学还要父母背着接送。
在历经种种痛苦和折磨之后,热爱写诗的余秀华走红了,诗歌带着她满世界地跑。
文章图片5
余秀华曾经在公开演讲时说过,自己能有今天,必须感恩父母,“他们付出了特别的爱,才成就了我乱七八糟的人生,和我乱七八糟的诗歌。”
2015年,当她得知母亲被确诊为肺癌,余秀华说“我的天真塌了”。余母治病期间,余秀华带母亲第一次坐了飞机,跟自己一起走遍全国各地。后来,余秀华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在《无端欢喜》中,余秀华这样写道:
我从北京坐飞机到武汉,因为武汉大雾,久久不散,晚点了三个小时……我背着两个包,还滑倒了一跤。我想,幸亏我妈妈没有跟着我,没世她如果看见了,该如何心疼?而她再也不会跟着我了……
她的死是一个洞,开始的时候如同爸爸的烟头烫在裤脚上的一个洞,看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洞越来越大。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惹这个洞,但是总是一不小心就碰上了……这个洞无法缝补,也没有填充物,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看一次疼一次,因为看的时候一定是当初烟头烫上去的悔恨、责怪和怀念。
有时候,我感觉飞机在这个窟窿里飞,火车在这个窟窿里开,人们对我的赞美和诋毁也都在这个窟窿里,但是它们合起来也如同一颗灰尘在这个窟窿里飘着。
面对亲情,常常不是一句爱或者痛可以说清楚的,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独一无二,并且珍贵的。
你对亲情,有缺憾或抱憾么?
为什么译员的翻译稿费那么低
有人将翻译稿费低归咎于体制,阴谋论式的认为是体制不想传播知识,所以才压低了翻译的稿费。还有人认为,不仅仅是大制度过分贬抑的问题,还因为个别出版社迎合市场,忽视文化,不尊重翻译家,开出极低的价格,肆意盘剥他们的劳动。微博上就有人这样写道:“最大跌眼镜的是三联沈昌文在接受采访时炫耀说,他喜欢找老翻译家,因为这些人都不好意思讨价还价”。
目前出版社给出的翻译稿费的确很低,英译汉,一千个汉字的价格仅仅在100多元,甚至几十元。按去年去世的优秀的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及的价格,一个优秀的译者大致在50-70,而是用在校学生的时候,甚至只需15元。
但是,中国大部分媒体、出版都已经市场化了,按市场价格给出价格,也是天经地义。即使从道义上来看,这种行为也处于模糊边缘。因为这与在市场上买菜,或者请工人搬家讨价还价并无太大差别,那些指责出版社的人,在菜市买菜的时候,也搜稿蠢会与菜贩讲价。
与翻译稿费可以做一个对比的是原创性稿件的稿费。现在知名的小说家,或者网络小说作家,依靠版权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即便是在传统媒体上写稿,评论、专栏千字300-400元的价格已经算很低了,但比起翻译的稿费,还是高了一个档次,可支撑起一般的城市生活。
所以,事情不在于出版社的道德水平怎么样,而在于出版社为什么敢于这么厚此薄彼?为什么这种对作者“残酷压榨”的现象没有出现在小说与专栏、评论领域?
首先,翻译市场是缺乏竞争的。出版社看中一本书后,与作者谈下版权,在大陆范围内就具有了排他性的权利。这个时候,无论翻译质量如何,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以自然没有动机去提高翻译质量。
其次,提升翻译质量本身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活,如果用经济学的概念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边际效用非常低。
英译汉市场,是一个门槛不高,但天花板却非常高的市场。一个英语6级的人,就能借助工具书,进行翻译。现在有了电脑,人工智能也在不断提升,效率就更快了,有些不负责的翻译公司在完成低端业务的时候,甚至是直接在Google翻译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一个好的译者,在传递那些字里行间的意思的时候,反复推敲琢磨,所需要的资历与脑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从能翻译,到翻译的非常好之敬袜间,差距非常悬殊。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切,读者却很难体会得到。读中文版本的读者,一般不会已读过原版,处于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很难从原著作者的意图、字里行间的潜在含义等角度对翻译质量做出判断。读者能判断的,仅仅是语句是否通顺,是否流畅。而且,即便连通顺、流畅都达不到,语句拗口,但汉语毕竟是读者的母语,阅读过程的顺带除错能力高,因此对译文质量的包容性也高,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抱怨。这就意味着译文的质量并不会对出版社产生太大的压力。
著名文学翻译家王智量曾谈到,他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稿费本该是按行数计算,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不到4万字的书,王智量总共才拿了600元稿费。
王智量家里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画像,旁边有其散文诗中的两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用俄语饱含深情地念完这两句话后,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给我的稿费,译这一句话,我只能得两角钱!王智量曾自嘲,他一天能翻译20行就不错了,才70元,还没有住院时医院的护工阿姨工资多。
文学翻译可以说是提升翻译质量边际效用小的典型例子。文学翻译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文学修养,无疑需要长期的积累,但最终体现的效果,却很难有客观的标准。“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苦苦推敲的意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的。再加上,很多中译本仅此一家,读者就更无法比较了,比如,王智量世陪他翻译的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目前唯一的中译本。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随着全民英语水平的提高,很多译者本身或出于兴趣,或由于工作,本身就需要通读原文,翻译对他们而言,就只是一件附带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们的要价会更低一些。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样出于兴趣或顺带的业余译者,拉低了整个翻译行业的价格。
所以,翻译市场上,好的产品,文化价值非常高,社会效益非常高,劳动成本更是非常高,但遗憾的是,市场价值却注定很低。市场本身存在失灵,而且,这种失灵相当顽固,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不能作出一些改善的努力。
总体上看,出版社能够压低翻译费用,是因为关于翻译质量的信息的评估与传递是缺乏效率的。那么,促进翻译质量信息的传递,就能帮助市场信息透明,从而提高优秀译者的报酬。比如,译者一定要强调自己的署名,打造自己的品牌。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一些网站、微博账号、公号来收集读者对外文翻译书籍的翻译质量的评价。还可搞一些奖项,或者用类似“金酸莓奖”的形式,对翻译质量极差的出版物做出批评。
希望能帮助到你,望采纳!!!
董卿朗读者说妈妈的王智量是谁
董卿朗读者说妈妈的王智量是知名翻译家。最新一期的《朗读者》的主题词是痛,节目请来了知名翻译家—唤配—王智量先生。老人家已经九十高龄了轿链脊,《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翻译的,至今还在出版。王智量在访谈中讲到了自己闭渗的成长的故事,没有吃的时候,常常是母亲不吃饭,养大了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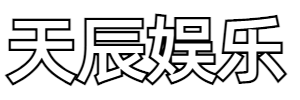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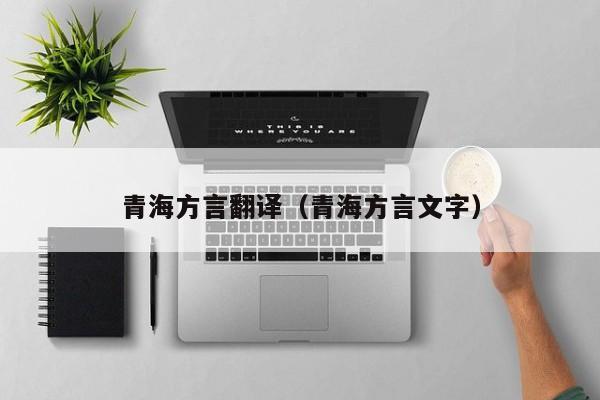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